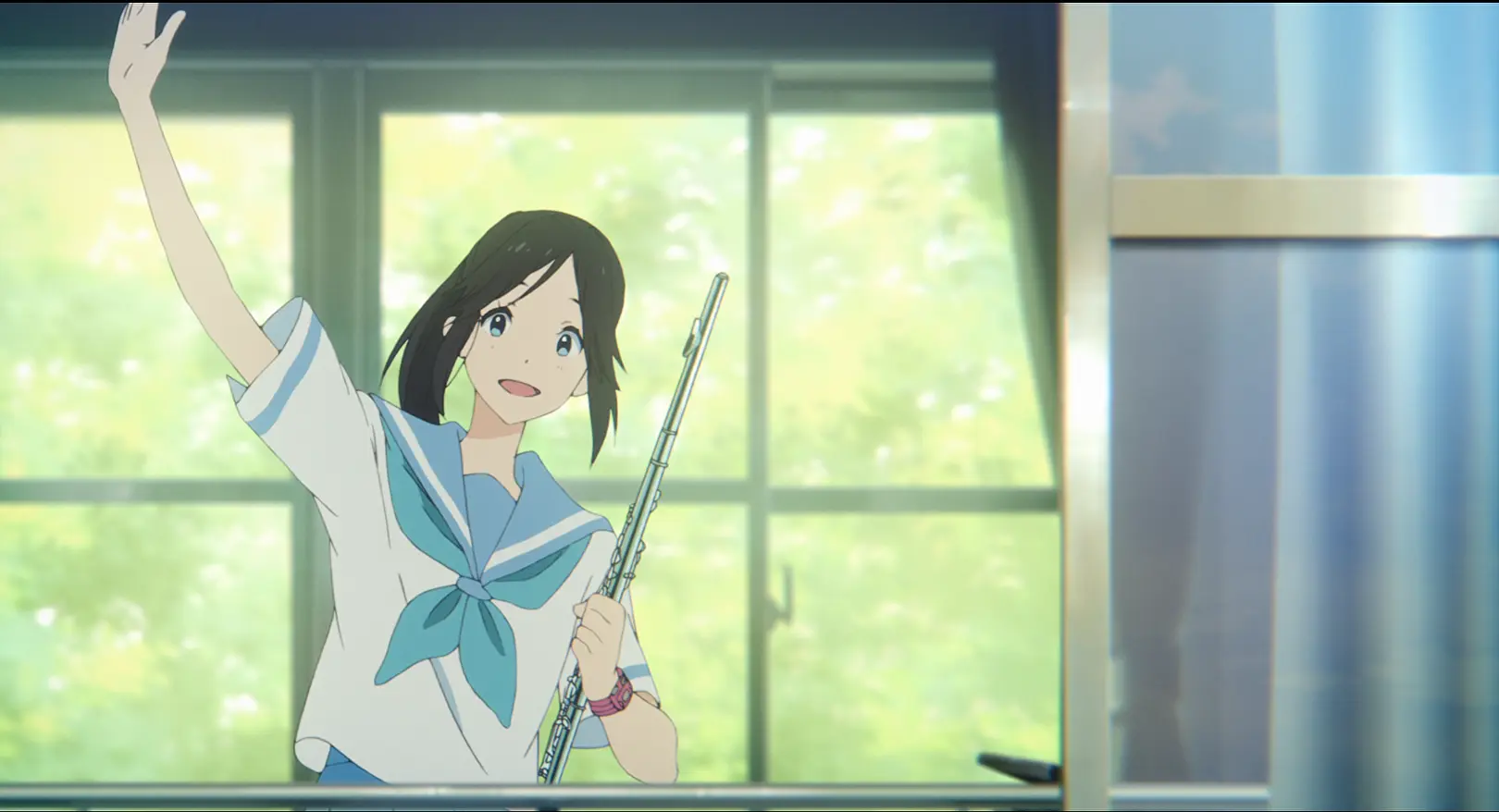>. Die Blechtrommel [blechtrommel]
>. Die Blechtrommel [blechtrommel]
The title comes from the fiction Die Blechtrommel.
華夏的文化傳統,向來是長者居於上的,可以說在從部族進化而來的過程中,最徹底的。優秀的,身強力壯的年輕者,是被普遍的道統制約著。然而一旦道統有一絲松動,率先奮起的卻依然是那些年輕人,這是普世規律,是千百年的社會學魔法產物。那我們是否就能說,1919年的那一場運動就是道統的又一次傾覆呢?可以是,亦不是。回顧考察五四的方方面面,我所看到的卻是驚人的保守性。 阪本龍一在《1919》一曲中全篇插入了列寧在紅場的講話,緊張的大提琴聲預示著風暴的正在形成。從宏觀世界史角度看,五四或許只是一場蘇維埃革命時隔一年多的余震,這和70年後,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劇作與行動所引發的地震是很相似的。但是自那一刻,自一零年代開始,中國的年輕人也真正開始創造歷史了。從浪漫主義運動開始,不知名的騎士摘下頭盔,長存在對美的永恒觀測中了。從1792開始,戰爭被革命所取代,人們驚恐地發現,流血與犧牲還可以超越民族和信仰的界限。有死在希臘的英雄,有死在烏拉圭的英雄,有死在無名的,充斥著硝煙味的古戰場的英雄,我們開始相信,人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烏托邦,這種烏托邦是純然超乎了莫爾的救贖色彩,亦是純然高於嗣後被權力所異化的美麗新世界的。這是全人類史上屈指可數的好時代,也是人類的青年時代。天所賦的權利已然足夠,法理在天,則自然也在人心,甚至這一個時代的哲學,都充滿了樂觀的不可救藥,霍布斯怎麼能和康德相比呢?懷疑論只是只竭力發聲的小蟲子罷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無數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這樣的樂觀在1919達到了高潮,經過百年確實的積累,我們意識到,烏托邦不僅是在法理上,哲學上,歷史的時間性此在上可行的,它在物質上也是可以有堅實基礎的。高潮之後的沉寂,我們已經不需要言喻。海德格爾所說的,偉大的衰敗也是偉大的,大體就是這個意思。 人類學上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大體上亦適用於中國。我之所以說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是保守性,便是因為上述的啓蒙進程,中國都沒有經歷。遭受苦難的他者怎麼能體會到殖民者的喜悅呢?彷彿他者對殖民者的效仿,勢必要經歷痛苦與流血的進程。那便是因這效仿的一切,本身也是掙紮的痛苦和流血所換來的,人類史上如此簡單的,等價交換原則。 五四的那些親歷者,他們都明白烏托邦的可實踐性,在認知上,世界上的人與人並無太大差別。但可實踐性並不是必然的實現,五四要做的,並不是把中國向美好的方向帶,而是要重走一遍殖民者的老路,是要把西方的偏差施加於「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文化上。因此我更樂意稱五四是披著1919皮的1789。 但是問題並不僅僅如此簡單。它所帶來的影響超乎了自身的想象,超出了自身的控制,並不僅僅是……它將在歐洲徘徊的幽靈請到了亞細亞的土地上,而在於,它讓那些煽動者懂得了利用年輕人,懂得了利用年輕人的一切……去實現自己的目的。五四可能未能實現一些預期目標,但驚人地,由於北洋的寬松處理,它沒有打斷中國緩慢的民主化進程。反觀70年後,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打斷了很多很多。即使他們並沒有做出什麼,沒有暴力,沒有沖擊,也沒有揪出那些眾矢之的的犧牲……他們僅僅是坐在了那里,拿著無比美好的生命開無比美好的玩笑……他們沒能理解危機的真正含義,他們只是唱着情歌。於是這一切變得無比可悲……變成了每一年的燭火,變成王小波筆下生命的巨大悲涼,變成海子的臥軌,變成時代的傷疤,變成亞利桑那荒漠中那塊墓碑。 於是自五四後,學生成了永恒的犧牲品,青年節成了偽裝與偽善的外衣,那十年是年輕人輸了,那三十年是年輕人輸了……那一個月,也是年輕人輸了,煽動者永遠不缺,而被煽動的學生一代又一代,有的見證了,有的離開了,有的帶著美麗化成蝴蝶,飛得很高很高。這樣的國家,又能說成長了嗎?在長者居於上的「我們」的世界中,1919真的來了嗎? 自18世紀以來……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場跑向烏托邦的歷史,五四在其中又有多少份量呢?五四在這片厚重深沉的土地上不停地上演,輪回。一百年,五十年,三十年,巨大的空虛感襲來,獨自爬到城墻上的黃昏,我們又見到了多少落日的軌跡?但是不可言說的厚重,不可言說的奔跑,即使無法被理解也依然存在著,這何嘗不是一種最好的隱喻,是最好的,獻給拜倫勳爵的詩句嗎? 擋在強權的車輪前的學生也成了一種隱喻,成了永恒的悲傷,而歷史的腳步飛快,把所有血跡擦幹,把自以為時代弄潮兒的無辜者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他是獨一無二的。 以上,五四百年有感。
對本真現實的虛構呓語,對不夜城裏衆人的一幅素描。 西郊有密林,助君出重圍。 時近午夜,她熄了大燈,重又坐到書桌前。宜家的廉價台燈並沒能完全照亮自己,這座城市的冬日深沈地襲入扁平的現代房屋,她打了個哆嗦,摸索著遙控器,卻不慎撞翻了余有湯水的方便面。 她懊惱著起身拿抹布時,瞟了一眼屏幕上時間,23:58。說不定來不及搶微信群裏的紅包了,她想。這該死的一年依然以該死的結尾收場了。 半個月前,她換了工作,坐了18小時火車,獨自來到北京市郊。短租房的價格並不便宜,在踏上首都土地同時,她就把找房子列入了待辦事項最優先的一欄。日複一日早九點的提醒慢慢讓她厭煩。在效率的神話上我又做到了什麼呢?心生的疑惑被一個個記下,時不時翻閱,卻連綴不成的詞句。 抹幹淨桌面同時,她聽到了蜂鳴器的報時,伴有接連的消息提示。她急忙拿起手機,機械又准確地點開飛速閃過的色塊,有時發上慣用的表情,劃著手指在鍵盤上打出應酬的話。 群發的祝福擠滿列表,她想不到什麼合適的詞句來回應這些陌生的朋友。躊躇了一會,還是用短信親自給幾個人發了祝福,有一個迅速回複了😊,余下則是未讀標簽的沈默。假期也不能太晚睡罷,她想,過了25歲,她們這代人沒有了熬夜的資本。 有空再看電腦已是0:03,她盯了一會這個數字。躍遷的世界誤入歧途,太好了,她突然發現最大的注意點是不能在填表時再用上那個逝去的年份,這是人腦落後的遲滯,其他的呢?「也許數字已經幫我們安排好了一切數字」。該被重置的數值在所有地方都被忠實地清零。 她戴上耳機,想聽首五月天,通知欄閃過一則疫情通報讓她不快。也許這個即將來臨的冬天比去年更加危險,不知怎地她抱有這個預感。我真的走出黑暗了嗎?又一陣寒意,她發現自己還是沒開空調。 城市解封一個半月後,他與留美朋友通了次 Skype,前一晚在微博上看到的視頻讓他有些緊張,他依稀記得發小就住在那之于他十分陌生的城市。 屏幕上淩亂的起居室還是讓他稍稍寬了心,大洋彼岸生活一切如常,甚至可能比這半年的此岸還好些。但露面的發小卻頗有變化,淩亂的胡子,披肩的長發,呈現出在家松散、跨落的生活。 大學停課後,他只出過兩次門,一次是沃爾瑪,另一次則是送發急病的鄰居老太太。「中國人都要謹慎不少,隔三差五從樓下經過的競選集會也沒有亞裔的影子。」 「在家嘛,也不怎麼講究,胡子一周刮一次也夠了……」朋友笑。這時,倚坐床沿的他聽到一聲似雷聲的巨響,從揚聲器傳出的真實感讓他一顫。對方也一定聽到了,他急忙跑出房間,少頃又回來,像寬慰了不少。 「還以為是拿著槍上樓了……你也知道了吧,波特蘭這幾天都不怎麼正常。」他帶著點憂慮,想說什麼,卻只點點頭,繼續聽朋友講。那些並不怎麼熟悉的選舉和平權運動,陌生又真切,仿佛另一個世界近在咫尺。 友人的一句話讓他回過神來:「還是國內好啊,前段時間怎麼搶機票都搶不到。」他並不太喜歡這句話,他覺得自己是被代表的,好的部分,就像創口貼一樣。 「下半年要是能回來,就去你們學校玩玩……」 「那也得進得來。」兩人笑。 「啊對了,你給寄點土産來吧,隨便什麼都可以。哦,有些應該會被扣,對,寄點榨菜吧,這邊早買不到了,沒了榨菜吃什麼都覺得少點味道。」 「那要什麼時候才能收到啊……哦,過年那會讓你代購的健身環咋樣?」 「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出門呢。」 哈哈,他笑,摸了摸半年肚子上積攢下來的贅肉,若有所思,可能對方也覺得他變了不少罷。 暗淡的星夜,接到房東電話。他走出大樓,叫了輛車,清秋的夜催促人們披上單衣。掠過窗外的霓虹漸漸亮起,今天下班早,但止不住疲累兒把他狠狠地按在後座上。他癱著,知道房東大概要說什麼,卻並沒做好准備。 與其思考對策,模型殘留的性能問題更讓他憂慮。他想象即將完成的這一單彙入數據流,飄上雲,互聯網接管了它,他盯著前座攝像頭,他的心能被服務器讀出嗎?何時能聽到機器告訴他,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旅客是帶著幸福在路上的? 這個數字真的有意義嗎?歸根到底,他想,「苦難依然是要自己咀嚼的」。要是網絡把他的情緒也一齊帶走就好了。他為自己冒出這個想法感到奇怪,畢業前已現端倪的躁狂仍困擾著他,狠狠捶了下座墊。紅燈,他聽見師傅給家裏發微信。 最後一晚躺在這床上,這終歸不是自己的家,行李箱攤散。他想著要寫點日記,起身拿過平板。想想,又點進那熟悉的微博,發了短短一句:今天被房東趕出去了,半年的房子連一個月也沒住滿,不好意思李醫生,讓你聽到這麼難受的事,晚安。一條條翻閱其他人的生活,人間明暗。 複又被顛簸震醒,他回味剛剛的夢。現在已經不知是好是壞。列車有力越過華北平原,窗外差次河流,給散居的村落輸血。對座有幾人聚著喝酒,散落在不鏽鋼盆裏的花生米。有個哥們像講到了傷心事,垂下頭幹號了幾聲。列車員推著餐車走過。 昨晚,他已經明白了不買臥票的錯誤,今年春節回來應該格外早,這確可讓家裏人吃一驚。他盤算,要不年後也晚點走吧,或者再也不走了。六七年前,他拼死拼活考到了上海去,除了做題,對那什麼也不懂。現在,他發現自己對故鄉已經什麼也不懂了。 隆隆地繞過山口,赫然現出渡月橋的影兒,暮色谒然,他伸了個懶腰,將我城的一切都抛諸腦後。 這篇文章寫於去年五月,因為一些原因在當時沒有立刻公開,現在基於補全的目的將拙作付梓於網路。以下是正文: 今天的我們會自然地使用各種設備上的中文輸入法,隨心所欲地運用拼音,注音或是五筆等標記方式表達漢語句子。這種便利性的理所當然,往往會讓我們忽視漢語融入現代信息技術過程中的無數艱辛不易。 信息技術的含義在世界範圍內並不具有普遍性,而互聯網的承諾願景可能永遠不會到來。今天的我們越來越認識到,作為現代文明基石的電訊技術,在傳播過程中必須與本土的語言、文化乃至政治語境協商,變化甚至對其妥協。這樣的過程是無法與血淋淋的經濟殖民效率相提並論的。西非的孩子接受信息技術教育同時,也必須潛意識地將學習法文和英文作為前置條件,這種隱形的文化不平等不斷加劇,表現在了諸如精英階層的西化和流失。儘管如此,班圖語族也在接受拉丁字母的文化殖民中得以保存,在條件更為良好的東亞,獨特的漢語文字在衝擊下屹立不倒,則更令人欣慰。 我們言說他者的技術史,並不是出於博物館藏式的獵奇心理,將異質的歷事看似包容地接納,實則緩慢地抹滅,而是為了將這種他樣的生活引入理所當然的日常,進而解構地重新審視均質化現代的殘酷。 我們在計算機上的輸入行為,和對前信息時代的工業出版的想象之間,被非常典型地割裂了。在歷史教科書中被介紹而熟知的活字印刷,又是如何演變為與標準 QWERTY 鍵盤相容的輸入法的?試着回想你腦海中打字機的印象,那一定是一個標準鍵盤佈局,充滿機械感地印製拉丁字母的造物。 在使用字母文字的文明中,擴展和改造美國人發明的打字機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德國人新加入四個字母,並固定直至如今的德語鍵盤佈局。聰明的工程師將列印杆(typebar)的方向加以調整,成功為書寫順序相反的希伯來語以及阿拉伯語帶來了信息時代的先聲。當然這種擴張也不得不遇到削足適履的境況。暹羅人為了能保留雙排打字機的結構,放棄了兩個字母,而它們也漸漸退出了書面語。 這樣的改造在遇到中文時完全束手無策了。可以說,當時的「現代」文明堅信着這種不相容是落後的體現。在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年代,語言學家宣稱漢語處於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間的未成熟期,激進的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興致高揚地討論漢語拉丁化的方案。 但是實際的傳播需求無法等待拉丁漢語的普及,在商務印書館的資助下,1926年問世的「舒式」打字機拋棄了鍵盤的設計,採用按壓式字模排布。這種誇張的樣式頻頻登上美國雜誌的諷刺漫畫專欄。但最終,「舒式」打字機獲得了市場認可,並不斷在便利性上得到改進。 受到統計語言學的啓發,字模的數量被壓縮至近三千個常用漢字的範圍內,而很多生僻的漢字也可以通過部首的組合被印刷出來。在之後被廣泛使用的「萬能」和「雙鴿」牌,都沒有脫離這個基本設計思路。 有趣的是,打字員的熟練程度在中文輸入中顯得更為重要。除了在數量上壓縮選字的耗時,聰明的打字員重新排布字模的順序,將常用的詞語放在相近的位置,大大提升了打字效率。例如在新中國早期,熟練的打字員也作為光榮的勞動模範得到宣傳和表彰,他們的排布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語言使用情況和意識形態。 這種做法的創新之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深入研究人機交互的視點,通過將規則性的語素加以組合,我們昭示了一種機器主動「學習」的可能,我們如今的許多輸入法,也帶有了根據個人詞頻重新排列的選字功能。而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四十年代,這種人機交互的思想也體現在了林語堂革命性的發明——「明快」打字機上。作為第一款中文電傳打字機,它採用了如今理所當然的編碼技術,將中文對應到數字列表,與之相近的還有同樣磕碰前進的中文電報技術。 更有意思的是,林語堂的打字機將漢字拆解為七十二個偏旁部首,使用者在同時按住兩個偏旁時,一個選字窗口會彈出相應的八至十個漢字供選擇。雖然這樣跨時代的發明沒有得到繼續資助,林語堂本人也因為瀕臨破產而不得不放棄繼續研製生產,但它作為保存漢字和文化遺產的理想,作為他者對殖民文化的融入與反抗,作為堅守符號主權(semiotic sovereignty)的嘗試,或許比起一場失敗的漢語拉丁化鬧劇,更值得被人紀念。 這種技術角度的檢視和思考,有助於我們跳出「語音主義」和「象形文字」的二元對立,在激蕩的一百年後繼續思考規避文化消弭的可能性。同時,人們也能更清楚地認識到,這種掙扎般的努力從未停止,不過從一種危機變成了主動維護的文化意識。 個人計算機發明後,中文編碼的規範化進程從打字機時代的資本與個人推動,變成了一項國家意志為代表的大型工程。我們已經從前信息時代的漢字危機挺過來了,而跨入信息時代的門檻也就相對輕鬆得多了。同時,東亞文字編碼的統一嘗試,和後殖民主義思考下對本土文化的重發掘,一起推動了 Unicode 的出現與普及。 這種自信心還體現在了對「中文編程語言」可能性的討論上。1964年,中科院在對 IBM 大型機彙編語言的簡單模仿和遷移下,開發了 BCY 語言。進入新世紀之後,E語言等本土編程語言的出現,更加推動了計算知識的普及,也為中文在信息基礎架構的構建中爭取了一席之地。 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來自臺灣的唐鳳在2002年基於 Perl 開發的文言文模塊。她為這個項目寫了一個埃式篩法的示例程序: 新近基於 Javascript 的 Wenyang Lang 在優美性上與之相比,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了。 同樣於之現實中漢語保存努力的艱辛嘗試,在理論角度,人類學跳出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思考框架的可能亦從未停止。庶民的技術史有其獨特的在地性。這種在地性卻往往會因為話語權的缺失受到損害,會因為被強行賦予身份的武斷受到曲解,有時甚至會因為粗暴的歐洲中心主義式解放被完全破壞。被完全國有化和農業機械化前,維持一個共有式平衡的宗族農業。受到代議民主衝擊的種姓制下吠舍等手工藝者,向既得利益的高種姓族羣的職責讓渡。都會在不被注意間抹滅原生的,鮮明的生命體驗。 相應地,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體現在遊戲開發與策劃中。在英雄主義的電子遊戲劇情脈絡中加入所謂「東方元素」,與為了跟上西方廣告文化而塑造的「打字機女郎」形象沒有多少區別。它們缺失了在全球視野下,對身邊事物的關切式理解。 將東西方簡單對立,只將自我作為現代的滑稽鏡像的思考方式,不僅僅存在於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本族精英,也體現在歐洲中心式左派的論調上。所謂文化「復興」的目標,產業化的一刀切式推廣,都隱含了一個現代文明作為普世標準的盲信,也常常刻意地忽視了全球性文明間的互相影響和學習。它們「代言」了庶民的生活本身,將這種美麗的歷時性現象符號化為了地緣政治中的鬥爭籌碼。 恰逢勞動節,而書寫這篇文章的另一個特殊意義在於,如何批判性地思考這個紀念馬克思所言的工業勞動者的節日,如何試着將遭到忽視的本土技術演進,在社會流動性之外使用「另一種」方式活着的庶民,以及他們對所謂「傳統」,對現代的貢獻,反抗和融入包括進來。而為了讓他們,讓我們被聽見和看見,一個參與式,直接民主的觀察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斯皮瓦克所言:「向庶民學習,以便設計出一種哲學或教育方法,使得人們在公共事務上能夠養成民主的習慣與機制。」 參考: 一路沿着小徑,秋意漸深,這條尋常的散步路徑少有人跡。轉過幾個拐角,不時有推着嬰兒車的年輕母親,草地上散落着她們的玩物。再走過一個分岔,已經不再有人聲,我留意着尋常的樹影,投射下來的美妙光澤,直到那張吊床出現在眼前。 睡是一個持久性的運動,它指向了人類最深處的情慾和陰鬱。在夢還未到來前,睡就是原初的混沌,邊緣系統極力抑制着皮質的活動,而未曾企及的目標——思考也被全然封鎖。在我之前的那具熟睡着的軀體,以一個不能再舒適的姿勢斜臥在吊床上。在一旁的草地上,橫陳着全部行當,大而鼓的旅行包,污漬斑斑的野餐墊及防雨布,和在最上面的深綠大衣。 神聖的睡把他的年邁掩蓋了,以至於我未能看清楚他臉龐上的皺紋。睡產生了美,而均勻的呼吸響應着日夜節律,一致,整齊地投射到觀者的心靈上。 他睡了有多久了?沒有人知道,睡的持久成了永恆,沒有任何異動和聲響能將他吵醒,在這一刻他就是世界的王。
她神經質地號哭着,尖銳地咒罵着一切她所能看到的東西,直到倦累,不再能支持自己站立。一旁的老松樹沙沙作響,悼念着已死和,未死的,不該死去的和死得其所的所有人。 歐羅巴的墓地都非常有意思,它們或設計獨特,或環境優美,抑或埋葬着大名鼎鼎的人物,所謂的「歷史」人物。墓地往往是開放的,在遵守禮節的條件下,可以自由地參觀和祭拜。著名的譬如魏瑪的諸侯墓地,布拉格的高堡教堂墓地,是相當值得一覽的去處。而有些墓地也鮮有人至,它們和被埋葬者一道,淹沒在深不可測的時間里。傳奇,或者是怪談滋生的小角落,永不能描述盡的苦楚,這些辭藻都不能概述這些散落着的墓地,它們的獨特之處。 已經渡過冥河的那些往生者,代替生者承擔哀傷的重量,他們一次也不會回頭。這是另一種生死觀,也是另一種先祖崇拜。 而那些在墓地里灑過的淚水,跳過的舞蹈,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在爲死亡做準備。我們只是未死者,而從不是不死者。
禮拜日的市場廣場(Marktplatz)有個人。 一個蓄着鬍鬚,背微駝的老人。他提着的環保袋空空的,四周緊閉的店門拒絕了行人的進入。他的毛料大衣微微翻起,但依然很得體地穿在身上。他步履蹣跚,但也頗有風度地走着。 他會給每一個街邊蜷縮着的流浪漢扔下硬幣,那些茫然卻又不哭訴自己境遇的人,街邊的風貌。他會逐步傾聽每一場即興演奏,小提琴,吉他,馬林巴琴,手搖風琴,乃至單純的鼓。他就這麼堅定地無目的地走着,走過每一個櫥窗,那些閃閃發亮的手錶,皮貨和珠寶。 在地鐵站的入口前,高高飄揚的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旗幟。幾個大鬍子的年輕人,高高舉起阿拉伯文的標語,散發着傳單。駐步的人不多,聚起的一小部分人群傾聽着她們的歌舞,他們的控訴,它的淚。 他也停下了腳步,望向那面旗,長久的,太陽西沉。
老市政廳總是有許多遊人,他們一波波地來,許多便是那世界著名的德意志老年人旅行團。事實上,爲游客中心做這些導覽服務便是一項很熱門的兼職。他們的講解當然幽默風趣,在歷史中穿插着段子和軼事,試圖讓這些離休後『享受生活』的老年人感到愉快。 聖夜臨近,臨時搭建的市場和裝飾已經完成,就算是新爆發的疫潮也沒能嚇退人們的熱情。同樣在這個時候,街頭可見的生態也越發拓廣,多數是樂音,連帶着一人集會,多人集會,一人表演,多人表演,一人娛樂與多人娛樂。 拐離主道,Thomaskirche 前的樹蔭稍稍幽靜些。這週五演奏的康塔塔海報貼滿了牆,啊,真想去聽一聽呢。 安靜的氛圍也會有安靜的表演。古希臘的劇場是表演和集會的場所,如果政治藝術也是表演的一部分,那一定是可在悠長歷史中追溯的傳統。嘿,瞧這是什麼的傳單,紅底上的那個標誌給無數人帶來了幸福和苦難。 能給出去的傳單不多,包容和歡迎顯然是兩回事。不過似乎,發放者和接受者也都不怎麼在意。紅色不是個討人喜歡的顏色,但是,我轉過身,新教的塔樓高聳,構成天際線的一部分。革命真的是這麼安靜的事嗎?
1. 他者的世界 [may-the-force]
2. 寫在年代之交 [covid]
3. 小型世界敘事 [hakoniwa]
4. 繞越 [surround]
躍遷
沈默的幫凶
繞越
5. 他者的技術史 —— 從打字機說起 [typewriter]
use Lingua::Sinica::PerlYuYan;
用籌兮用嚴。井涸兮無礙
。印曰最高矣 又道數然哉。
。截起吾純風 賦小入大合。
。習予吾陣地 並二至純風。
。當起段賦取 加陣地合始。
。陣地賦篩始 繫繫此雜段。
。終陣地兮印 正道次標哉。
。輸空接段點 列終註泰來。
6. 阿勒曼尼亞群像記 [alamannia]